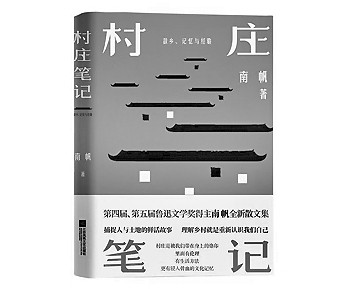调查问题加载中,请稍候。
若长时间无响应,请刷新本页面
【文学里念故乡】
作者:南帆(散文家)
很长一段时间,“故乡”在我心目中并不是一个情深义重的概念。故乡的景象、习俗、食物、乡音汇成地域文化,然而,地域文化会不会成为放眼四方的局限?我倾心于万物的普遍意义,对于京派、海派之类区分相当迟钝,更没有兴趣搜集大江南北五花八门的食谱与菜系。记住水的分子式是H2O或者勾股定理的“勾三股四弦五”即可,加上一个“故乡”的定语又会增添哪些意义?
故乡意识相对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,我始终居住在故乡。散文之中偶尔提到“我所居住的城市”,事实上也是我所出生的城市福州。福州是一个不大的盆地,我的寓所每一个窗口都看得见钢蓝色的起伏山脉,这儿距离东海还有数十公里,大比例的地图上看起来像是一个搁在海岸边缘的城市。除了若干年的下乡插队、异地就读,我一直居住在福州。福州气候温润,雨量充沛,夏季多半有一两次台风登陆,进入冬天,树木上的绿叶仍然茂密闪亮。两千多年前,这儿是闽越国的地盘。如今闽越人已经杳无音信,这个城市居民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北方的移民。魏晋南北朝以来,中原一带的人口开始大规模南迁,一些族群扶老携幼陆续聚拢到这个盆地安居乐业。这些移民性格之中似乎存有“说走就走”的基因。一些收不住脚步的移民漂洋过海,跨过海峡登陆台湾,或者顺风顺水到了东南亚一带。我的祖先五代时期跟随闽王王审知,从河南的固始征战至福州,在闽国建立之后似乎当上了掌管财政的大臣。作为一个“不肖子孙”,我的身上怎么也找不到金融家的气质。数十年的时间,我几度有机会移居外地,却又阴差阳错耽误了。有一天我惊醒似的问自己:老祖宗那种“说走就走”的基因已经在我身上失传了吗?我既不想刻意浪迹天涯,也未曾承诺踞守故乡。之所以至今栖身于那些钢蓝色山脉的屏风后面,顺其自然罢了。不论故乡还是异乡,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心安理得就是留在这个地方的最大原因。
鳞次栉比的高楼,明灭闪烁的霓虹灯,车水马龙的街道,大部分城市如此相像,福州也不例外。可若是异乡人踏入福州的地盘,便立即会陷入一个奇特的声音世界——巷口晒太阳的老太婆、肉铺子的老板或者水果摊的女主人正在说些什么?他们的语言似乎来自另一个发音体系。福州方言声调低沉,口音独特,异乡人的耳朵将遭受严重冲击。这种语言与标准的北京话相距太远,以至于丧失了猜测的可能性。起初,我对于方言没有多少好感,仿佛是小地方的可笑印记,不登大雅之堂。使用方言朗读哲学著作、法律文件或者数学公式、物理学定律,会让听众深感别扭。方言不适合阐述普遍的公共命题,只能在一小块地皮上流通——只能形容本地风味小吃的口感,叙述婆媳不和的家长里短,或者用于菜市场砍价。换上一口方言,仿佛背过脸逃离公共社会,返回渺小的乡土共同体。方言可以潜入一个地方的世俗角落,呼吸到种种烟火气息,交谈双方显得亲密、琐细、体贴,但是找不到气势恢宏的历史。后来我才明白,这种感觉多么错误——方言恰恰是历史脉络的见证。当年中原移民陆续南下,同时带来一波又一波的语言潮汐。各个时期的中原古音如同种子播撒在广袤的南方土地,逐渐演变为五花八门的方言。福州方言存留大量古汉语遗迹,例如称“你”为“汝”,“他”为“伊”,“锅”为“鼎”,“筷子”为“箸”,“如何”为“何如”。方言吟诵的古典诗词音韵铿锵,古意盎然。福州人林则徐讲不好京城的官话,据说道光皇帝声称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林则徐说官话”。坊间流传许多林则徐说官话的有趣段子。这又有什么关系?他老人家的方言口音威风凛凛,一声令下,虎门销烟。持一口福州方言,仍然可以闯荡四海,放眼世界,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转换为流利的英语,例如福州人严复。严复年少时就读于福州的船政学堂,继而留学英伦,翻译了《天演论》等诸多名著。他的各种头衔之中,翻译家排在一个相当靠前的位置。来自福州的另一个翻译家林纾更为神奇。他不谙外文,竟然翻译了一百八十多种西洋小说,以至于“林译小说”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专有名词。还原这些历史人物的方言口音,他们仿佛悠然跨出教科书,徜徉于附近的大街小巷。这时,故乡的形象开始在我心目中矗立。我告诉自己,故乡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,不要自以为是,一叶障目。
故乡产生过哪些耀眼的性格?这个问题将我的目光转向了三坊七巷。这个区域聚集众多名门望族,遗留数百幢古老的大宅院。林则徐与严复都曾经居住在这里,他们的宅院仅仅相距几步路。穿行于窄窄的巷子,石板条铺就的路面光滑如洗,厚厚的木门与雪白的风火墙背后锁住无数秘密。如果说繁闹的街道属于城市的浮华表象,那么,街道背后的巷子往往隐藏了城市的幽深。街道上的车流、喇叭、匆匆行人、商店的橱窗或者小摊上叫卖的吆喝无非临时景象,寂静的巷子细心将一些碎片收藏起来,沉淀下来,慢慢形成城市的另一种纹路。我即是在一条巷子的边缘偶遇林觉民。这是三坊七巷之一的杨桥巷,如今已经开拓成街道。林觉民住过的大宅院就在巷口,现在是林觉民纪念馆。
我在《辛亥年的枪声》这篇散文记录了一个意外的触动:当我四十八岁的时候,一个只活了二十四岁的生命不由分说地闯入,扰乱了我庸常琐碎的日子。我时常路过林觉民纪念馆,那一天突然被林觉民二十四岁的面容深深吸引。他的形象既单纯又复杂。黄花岗烈士义薄云天,绢帕上《与妻书》愁肠百结,国事与家事的矛盾交织在这个男人的内心,块垒难消。林觉民结交许多侠客义士,身上涌动着逼人的英豪之气。但是,他并非独往独来漂泊于江湖,而是始终放不下大宅院里的爱妻陈意映。这个人物既慷慨激昂,又儿女情长,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家,又是一个缠绵悱恻的情种,我从他身上发现了故乡深处闪亮的性格。只要有一个林觉民,故乡就值得放手书写。沿着林觉民的线索,我又在三坊七巷找到了沈葆桢、沈瑜庆、沈鹊应、林旭、林长民、林徽因等一干人物。他们的历史功绩盖棺论定,但是,他们那种神气活现、大开大合的人生姿态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我终于意识到,这一批人物是故乡对于文学的慷慨馈赠。
我曾经撰写一篇五万多字的散文《马江半小时》,叙述一百多年前中法之间的马江之战。许多历史著作完整记录了晚清的这一场战事。从清廷的左宗棠、沈葆桢、李鸿章、张佩纶、曾国荃到一批地方官与福建水师将士,这一场战事涉及众多人物,各种线索缠绕交叉,诸多传说真伪莫辨。探索这一场战事内部存在的空隙、悬疑和各个群体之间的落差是撰写《马江半小时》的动机之一。这一场战事发生在闽江下游一段称之为“马江”的江面。水流湍急,烟波浩渺,闽江盘旋在这一部作品的字里行间,成为众多传说与历史人物出没的舞台。完成《马江半小时》之后不久,我的寓所迁到江边,闽江日复一日流淌在窗前。“一条大江穿城而过”不再是一句概括的形容,而是时刻可见的事实。这个事实时常敦促我必须为奔流不息的江流再写一些什么。坐在临江的窗口有时会恍然觉得,身后的城市正在摇摇晃晃地沿江漂浮。我知道城市的街道与绿树之间穿插着四十多条内河,这些内河分别与闽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亲缘关系,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这条大江的消息。
我的《与大江为邻》这本小书零散记录了与一条大江比邻而居的日常景象:江流,潮汐,滩涂,白鹭,码头,江风,洪水,拉索桥,各种型号的船只,雕像一般的钓鱼者,沿着江岸跑步、跳舞与放风筝的人……离开窗口的取景框,可以寻访下游两岸的古炮台,炮台设置一道又一道火力网,封锁来自海洋的炮艇。如果将目光转向上游,可以看见江岸山巅的古塔,江流之中大坝拦截的水库,淹没在水库下面的村落,江流途经的山间古城……可以一直上溯至武夷山众多山脉簇拥的那一注称之为源头的水流。滔滔洪流,逝者如斯,然而,“江月不随流水去”,种种历史往事陆续沉积为地方的记忆。从武夷山到出海口,闽江的长度不过六百公里左右——长江的长度六千多公里。对于我的窗口说来,六百公里与六千公里区别不大。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饮。写作《与大江为邻》的时候,我想起许多事情来:少年时代泡在江里游泳,母亲与外婆曾经逃难到闽江上游的山城,父亲与母亲相识于江畔,后来又双双迁往闽江上游的一个小村落。伴随这一次写作的是另一个小小的自问:我的视野之中,为什么这一条大江姗姗来迟?这一派汹涌的大水难道不是故乡之中最为显眼的标记?
我不想过多责怪自己的迟钝。凡事皆有时机,故乡会找到各种机会恰当地展示自己。既然我一直住在这里,那就不必着急,耐心的等待必有所获。我的心目中,故乡曾经是一个符号,仅仅承担组织句子的功能,后来演变为意识的一个焦点,承担组织情感与记忆的功能。当然,我还有更多的期待——期待故乡酿造与组织各种瑰丽的想象。这时,故乡将会进一步成为文学生命的栖居之地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5年04月09日 14版)
阅读剩余全文()